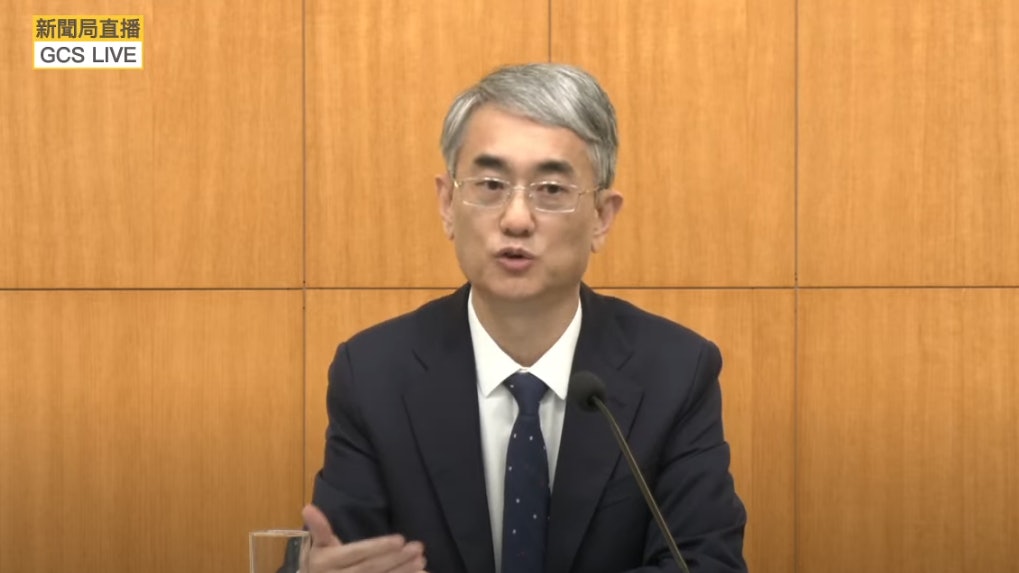年復一年,澳門的春夏之交總帶著一種特別的氣息,那是屬於「現金分享」的季節。這份從天而降的「福利」,早已不是單純的歲末分紅,它更像是這座城市與居民間一份心照不宣的約定,一份共享經濟成果的體現。然而,當這份約定遇上經濟下行、公共資源應當如何分配的現實拷問時,新的討論與調整便應運而生。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關於「省公帑增福利」以及對未符「183天」居住要求的居民說出「叫佢哋返嚟」的表述,無疑是這場討論中最具象徵意義的一塊石頭,投入了輿論的湖面,激起了陣陣漣漪。
這不是對單一政策的微調,而是對澳門社會福利理念、公共資源運用原則,甚至是對「誰是澳門居民」這個身份背後責任與權利的重新審視。當財政不再像過往那般寬裕,如何讓每一分公帑都能發揮最大效益,精準地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同時又不失公平與溫情,成為擺在政府面前的必答題。張司長的發言,正是回答這道題時亮出的一個關鍵面向。
現金分享:從共享成果到社會支撐
自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以來,澳門特區政府推出了現金分享計劃,初衷是為了紓緩居民面對經濟及通脹壓力的困境,同時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最初的發放金額是永久居民五千元、非永久居民三千元,隨後逐年增加,到二零一九年起固定為永久居民一萬元、非永久居民六千元。這份定期派發的款項,在過去十多年裡,確實為不少家庭提供了實質的經濟幫助,尤其對中低收入階層而言,更是一份重要的社會支撐。
然而,隨著澳門經濟結構的單一性在面對外部衝擊時顯得更為脆弱,以及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面臨壓力。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公共開支進行審視和優化成為必然。張永春司長提出的「省公帑增福利」方向,正是將有限的公共資源進行更精準的運用,將節省下來的資金用於改善其他民生福利,例如調升養老金、敬老金、殘疾津貼、失業津貼金額,以及發放育兒津貼等,以更精準地幫助弱勢群體和促進社區經濟發展。這顯示政府希望從普惠式的「派錢」,轉向更具針對性的社會援助體系。
183天:新的門檻與豁免
在此次現金分享計劃的調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增了居住條件:居民去年必須至少身處澳門達183天方符合領取資格。這是自二零零八年計劃實施以來,首次引入居住時間限制。在此之前,只要持有有效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即使長期身處外地甚至移居海外,也能領取這份現金分享。
這個183天的門檻,顯然是希望將公共資源更聚焦於那些「真正與澳門有緊密聯繫的人」,那些身處澳門、感受到本地經濟環境,並可能在本地進行消費以促進社區經濟的居民。背後的邏輯在於,如果現金分享的目的是為了紓緩本地生活壓力並刺激本地消費,那麼對於長期不在澳門居住的人士,其享受這份福利的合理性便受到質疑。
然而,任何單一標準都難以涵蓋複雜的現實情況。政府在設定183天門檻的同時,也考慮到了一些特殊情況,並設立了豁免和聲請機制。例如,未滿22歲且父母一方符合資格的人士、收取殘疾金或殘疾津貼的人士可以獲得豁免。此外,對於因特定原因身處外地的人士,如在內地養老、年滿65歲人士、在外地升學或住院等,可以向政府聲請將逗留在外地的日數視作身處澳門。值得注意的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工作或居住的人士,其逗留日數也可視為身處澳門,但同為大灣區城市的香港則不在豁免之列。
「叫佢哋返嚟」:語氣背後的複雜性
張永春司長在談及不合資格的朋友時,那句「叫佢哋返嚟澳門啦,同大家一齊啦」,雖然語氣看似輕鬆,卻在社會上引發了不同的解讀。這句話可以理解為一種期望,希望澳門居民無論身在何處,都能與這座城市保持聯繫,共享其發展與生活的點滴。但換個角度看,它也帶有一種勸喻甚至暗示的意味,似乎在說,如果想繼續享受澳門的福利,那就回來居住吧。
這句表述的複雜性在於,它觸及了澳門居民身份認同的深層問題。澳門居民身份證不僅僅是一個法律文件,它承載著歷史情感、家庭連結以及對這片土地的歸屬感。許多澳門居民可能因為求學、工作、家庭原因或養老而選擇在境外居住,但他們仍然視澳門為家,與家人朋友保持緊密聯繫,甚至定期回澳。對於這部分人群而言,將福利與居住時間嚴格掛鉤,可能會讓他們感到被排除在外,彷彿他們的「澳門人」身份因為地理距離而被稀釋。
而且,這句話也忽略了現實的複雜性。並非所有不在澳居住的居民都能輕易「回來」。學業、工作合約、醫療需求、家庭負擔等都可能是制約因素。簡單一句「叫佢哋返嚟」,未能體恤這些個人境遇,也可能讓人感到政府在處理社會福利問題時,缺乏應有的人情味和彈性。
節省的公帑:效益與公平的平衡
政府強調,實行183天的居住限制並非為了單純地削減開支,而是為了將節省下來的公帑更有效地用於提升民生福利。這個說法合情合理,在財政壓力下,公共資源的優化配置是必要的。將有限的資金用於增加養老金、殘疾津貼、育兒津貼等,確實能更直接地幫助到澳門本地的弱勢群體和有需要的家庭。
然而,這也帶來了關於「效益」與「公平」如何平衡的問題。對於那些長期在外地但仍與澳門保持緊密情感和經濟聯繫的居民來說,他們可能認為自己作為澳門發展的貢獻者(例如在澳門工作多年積累財富後移居外地養老,或在海外為澳門贏得聲譽的留學生),理應繼續享有部分福利。而政府將其福利權利與過去一年的居住時間嚴格掛鉤,是否完全公平?如何界定「與澳門有緊密聯繫」?居住時間固然是一個客觀標準,但情感、文化、經濟連結等更為複雜的因素又該如何衡量?
此外,關於豁免情況的設置也引發了一些討論。例如,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或居住可豁免,但香港卻不在此列,這是否合理?這是否考慮了港澳之間長久以來的人員流動和緊密聯繫?這些細節的差異,往往會影響政策的公信力和居民的接受度。
未來的方向:持續檢討與溝通
張永春司長提到,政府已經多方面聽取了社會各界對現金分享的意見,並且明年的現金分享計劃在沒有意外的情況下都會延續今年的條件要求。這表明政府對此進行了研究和討論,也預示著這一新的發放條件將會持續。
然而,正如任何公共政策的調整一樣,這次現金分享條件的改變,必然會在社會上引起討論甚至爭議。政府在強調精準施策、優化資源的同時,也需要更細緻地考量不同群體的實際困難和感受。對於因正當理由無法滿足居住要求的居民,聲請程序是否便捷、透明?豁免範圍是否足夠全面,涵蓋所有具有合理性的情況?這些都是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檢討和完善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政府與居民之間的溝通需要更加深入和坦誠。解釋政策調整的必要性固然重要,但傾聽居民,特別是那些受政策影響較大群體的聲音同樣不可或缺。理解他們的不便、擔憂和期望,並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更具彈性的解決方案,才能讓這項牽涉到幾乎所有澳門居民的政策調整,最終獲得更廣泛的理解和支持。
重新定義「澳門人」的福利
張永春司長的這番話以及伴隨而來的政策調整,實際上是開啟了一場關於如何在這個新的經濟環境下,重新定義「澳門人」應享有的社會福利的討論。它迫使我們思考,在財政不再充裕時,福利的優先次序是什麼?誰應該是公共資源最主要的受益者?而那些因為各種原因暫時不在澳門的居民,他們與這座城市的連結該如何被承認和衡量?
從「普惠共享」到「精準扶助」,再到與「實質居住」掛鉤,現金分享政策的演變,映照出澳門社會在不同發展階段所面臨的挑戰和選擇。這次調整或許會讓一些人感到失望或不便,但如果節省下來的公帑確實能夠有效轉化為更有針對性、更能提升弱勢群體生活品質的福利措施,那麼這或許是邁向一個更加公平、更具韌性的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一步。
結語
張永春司長關於現金分享的最新表態,以及隨之而來的183天居住要求,為澳門社會帶來了一個重要的公共議題。這不單關乎一份現金,更關乎公平、效益、居民身份認同以及政府施政理念。在澳門努力適應新的經濟常態之際,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如何在精打細算公共資源的同時,不失對居民的關懷與溫情,是特區政府必須持續面對的考驗。而那句「叫佢哋返嚟」,或許更應被視為一個提醒:無論身在何處,澳門的居民應當思考自己與這座城市的關係,以及如何共同應對未來的挑戰。這場關於福利分配的討論,遠未結束,它將伴隨著澳門的發展,不斷深化。